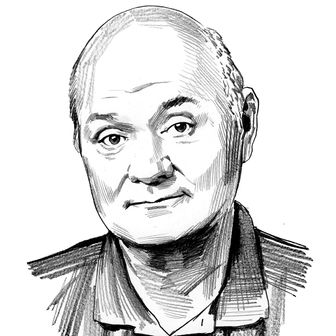阿斯卡这家餐厅今年冬天早些时候在威廉斯堡(Williamsburg)开业,乍看之下,它就像我妻子听腻了的那家布鲁克林风格的新餐厅的漫画版。在略显昏暗的主用餐区,只有七张桌子,占据了与餐厅相同的空间亲属工作室在威斯大道。服务员(大多是男性)穿着格子衬衫,留着精心修剪的伐木工胡子,对布鲁克林的热门话题有大量的了解,比如奶酪制作、晦涩的腌制技术和手工啤酒。餐厅里有一位著名的鸡尾酒大师,因为斯堪的纳维亚美食在布鲁克林(乃至全世界)都很流行,主厨当然也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如果你不坐在酒吧间里,这里的特色用餐选择是一份季节性的品尝菜单(六道菜65美元),因为我们正处于严冬,它包含了玫瑰果、卷卷地衣和根茎类蔬菜等苦行食材,厨师们自豪地在厨房的一个小铜锅里培育这些食材。
但就像这个美食狂热区涌现的许多餐馆一样,Aska的经营比看上去更复杂、更世故。鸡尾酒大师(也是股东之一)是埃蒙·罗基(Eamon Rockey),他从曼哈顿来到布鲁克林,在那里他负责饮料项目Atera并帮助开发饮料麦迪逊公园11号.主厨Fredrik Berselius曾在纽约几家豪华厨房工作过。烧酒,本身之后,他又在同一地点开了一家名叫Frej的餐厅,虽然时间不长,但好评如潮。他与瑞典厨师马格努斯·尼尔森(Magnus Nilsson)不相上下,后者用各种原始的食材(猪血、牛骨、潮湿的森林树叶等)调制出奇异的美味佳肴。在这个国际化的城市里,他的烹饪与尼尔森(Fäviken)在他位于瑞典北部荒野的著名狩猎小屋提供的那种原始的土食美食最为接近。
至少我是这么想的,一边琢磨着那对深红色的饼干似的东西。我们的伐木工人服务员温和地告诉我们,这两样东西大部分是用脱水的猪血做成的。它们尝起来有点像铁锈,就像新鲜的血液一样,带有一种农场猪肉的回味,我们用一种名为Next of Kin的aquavit产品尽快把它们喝下去,它尝起来像斯堪的纳维亚版本的薄荷朱勒酒,用红茶菌和香菜而不是薄荷调味。其他的餐前“口味”还包括炸梭子鱼皮薯片,蘸着糖蜜和烟熏自制奶酪的薄酥饼。然后,刚烤好的香菜卷从厨房端了出来(配上一层美味的自制黄油),接着是第一道菜,是一对热乎乎的长岛牡蛎,Fäviken风格,放在一个陶碗底,里面有黄瓜,闻着莳萝的味道,还有一勺牛油。
与马格努斯·尼尔森(Magnus Nilsson)不同的是,这家布鲁克林小餐馆的厨师并不是在占地2万英亩的大庄园里为你准备晚餐。但他们做了一项令人钦佩的工作,他们让你感觉自己与户外的各种烹饪有了联系,以一种柔弱的、有礼貌的、祭司般的方式。我们的服务员煞费苦心地说,前面提到的长岛牡蛎是“手工采集的”(而不是人工养殖的),然后是一条鲱鱼,厨师们把鲱鱼拆解,分开烹饪,重新摆放在盘子上,形成一种从头到尾的雕塑,配上新土豆、小枝绿色植物,以及脆脆的炸尾和炸头。下一道菜是根类蔬菜(红薯、地衣卷)的覆盖物混合物,配上一个鸡蛋的蛋黄,尝起来有一种淡淡的药物的味道,尽管用我的一位喜欢在城市生活的客人的话来说,它看起来就像“暴雨后树桩的水坑里能找到的东西”。
不可避免的是,阿斯卡的一些苦行僧混合物并不那么可口。
我不喜欢某天晚上吃到的萝卜丝和咸鱿鱼,也不喜欢厨房盘子里那块坚韧的、微微像橡胶一样的大鲳鱼,配上花生酱色的糊状卷心菜purée。这个冬天,贝塞利乌斯选择的蛋白质似乎是猪肉,尽管他提供了几块很吸引人的肉(猪蹄、肋骨、猪颊肉、猪肚肉),但令人称赞的时令配菜(乳清发酵的芜杂甘蓝皮、烤干草的淡淡的精华)往往会掩盖肉天生的猪肉味。唯一的例外是脂肪丰富、去骨的猪蹄,用苹果加糖,还有经典的瑞典土豆饺子,厨师用土豆泥和五花肉做的,à单点供应,浇上一层潮湿的烟熏农民奶酪,用茴香叶和越橘调味。
在Aska的酒吧里吃一顿美餐是有可能的,我去的那天晚上,那里的菜单包括红烧牛腮肉、一盘盘本地半壳牡蛎(当然是手工采摘的),还有两种不同的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热狗。你可以用Rockey的古怪鸡尾酒或各种精心挑选的苹果酒、波特酒和黑啤(来一瓶咖啡浓的瑞典波特酒Dugges 1/2 Idjit!)来配你的饺子)。只需40美元,Rockey就会为你的每道菜搭配葡萄酒和烈酒;我们享用了美味的朗格多克-鲁西永白葡萄酒配牡蛎,还有用洋葱和鲱鱼调味的冰冻水维特。甜点是一勺小豆蔻冰淇淋,外面裹着用榛子碎和棕色黄油做成的慕斯。我依依糊糊地记得,这道菜很好吃,还配了一杯Bodegas Dios Baco奶油雪利酒。
阿斯卡
威廉斯堡威斯大道90号,N. 11街;718-388-2969
小时:晚餐周一至周五和周日下午6点至凌晨2点,周六至凌晨4点。
价格:六道菜的试吃菜单65美元;à点菜,6至12美元。
理想膳食:牡蛎,鲱鱼,猪蹄配苹果,土豆饺子,小豆蔻冰淇淋。
注意:主餐厅周日至周四提供试吃菜单;周五和周六提供à点菜菜单,酒吧随时供应。
便条簿:一个是热情的斯堪的纳维亚式烹饪,另一个是布鲁克林的价格和饮料。
摄影:Victor Prado/《纽约杂志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3年2月11日的《纽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