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传说,我以前那家餐厅的几个垂头丧气的常客,乔小。这家餐厅过去只占据了第六大道和第12街东南角的一个狭小空间,现在它还喜欢讲服务员路易死于心脏病的那一次。就像城市中许多消失的咖啡店、小餐馆和速食餐厅一样,Joe 's对经常光顾这里的人来说是一个松散、欢乐的俱乐部。我会看到电影导演约翰·沃特斯(John Waters)站在柜台前,穿着熨得整整齐整的西装,一本正经、彬彬有礼地喝着咖啡。艾萨克·米兹拉希在电视出现之前是这里的常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个记录大城市怪人的伟大编年史家也是《纽约客》作家约瑟夫·米切尔,他经常戴着灰色的软呢帽时不时过来。
路易是小乔餐馆不可或缺的负责人,一个令人生畏的maître人物,就像马戏团全盛时期的西里奥·马乔尼(Sirio Maccioni)一样,知道所有常客的怪僻,并给每个人安排好自己的位置。他知道我喜欢坐在柜台的两头,独自享用下午的blt三明治(多加蛋黄酱),而我的小女儿佩内洛普(Penelope)喜欢她平时喝的鸡汤(盛在碗里,多加饼干),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喜欢。当醉汉从街上踉踉跄跄地走进来的时候,他维持着秩序。他有一种技巧,能让不太循规成矩的村里常客平静下来,比如“纹身女士”,她的脸上布满了复杂的纹身图案。还有一位常客,当她被世界的忧虑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有个习惯,就是大声喊出她的正常秩序——“八杯咖啡,淡而甜!”——她声嘶力竭地说。
路易去世的时候,乔餐馆的许多常客都非常震惊,他们跑到外面去守灵。当他们到达皇后区的殡仪馆时,餐厅的员工——快餐厨师,留着蜂窝状发型的女服务员——穿着一身黑坐在打开的棺材前。他们脸上都带着严肃的表情,但当他们熟悉的顾客鱼贯而入时,房间里的气氛变得欢快起来。他们开始互相耳语。《威士忌先生,培根的两面》;“这是炒蛋夫人,烤百吉饼”;‘这里有BLT三明治,没有梅奥酱,’”一位前来参观的忠实常客回忆道。“乔的家庭是一个有趣的不正常的家庭。我觉得在那里很安全。我在帕维翁餐厅吃得再好不过了。”
Joe Jr. s在2009年夏天关门了,窗户上匆匆钉了一张告别便条,解释说这家餐厅已经失去了租约,经营了30多年的他们正在说再见。就像Henri Soulé著名的法国餐厅一样,它最终被一个更时尚的版本所取代:café提供巴西咖啡,新一代戴着耳机的habitués挤在不舒服的木椅上,静静地盯着他们的笔记本电脑,用可生物降解的纸杯喝着4美元的咖啡。有一段时间,普拉特一家试图在我们的小社区里另找一家地方吃家庭早餐,但老式餐馆和咖啡店的数量越来越少,要么太拥挤,要么太无名,要么太遥远。如今,当我的女儿们想要一碗鸡汤时,她们会去街边的普瑞特马槽(Pret a Manger)买到。尽管我有时会在街上路过如今身材苗条的米兹拉希(Mizrahi),但我再也没有见过约翰·沃特斯(John Waters)或纹身女士(Tattoo Lady)。

和大多数大灭绝事件一样,大型餐厅、咖啡店和小饭馆的消亡已经在我们身边慢慢展开了几十年,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根据一个非常苦恼的克雷恩的根据几年前的一份报告,该市卫生部列出了大约400家带有这句话的餐馆用餐者而且咖啡专家说,在他们的名字里,这个数字比上一代的1000家有所下降。(许多新咖啡店的名字里并没有咖啡。)就像五六十年代的老式自动贩卖机和自助餐厅,以及更早的一代经典犹太熟食店一样,小餐馆的衰落有很多原因:租金和地价飙升;不断上涨的食品价格;一种更权宜之计的、高雅的和粗俗的咖啡文化的传播;整个世代的邻里“常客”都在慢慢地、无情地变老;要让一份古老、杂乱、长达十页的菜单与时代变化的口味保持一致是很困难的;还有将家族企业传给新一代企业主的挑战,他们中的许多人受过大学教育,可能更喜欢在咖啡吧消磨时间,而不是在热炉子上打鸡蛋。
在沉迷于舒适食物、原产地单一的一代中,哀悼这种古老的用餐文化的逝去已成为一种时尚。在过去的几年里,这种关闭已经蔓延开来,从曼哈顿(著名的咖啡馆爱迪生在剧院区,La Taza de Oro在切尔西,格拉梅西公园(Gramercy Park)的抒情餐厅(Lyric Diner)),到郊区(格雷夫森德(Gravesend)的Del里约热内卢餐厅(Del里约热内卢Diner)格列柯在羊头湾(sheephead Bay),食品媒体和博客上的哀叹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但在这个充满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选择的世界里——从25美元的厨师汉堡,到你喜欢怎样滴埃塞俄比亚咖啡,你想在里面倒什么颜色的杏仁奶,到你想要哪种手工猪肉,应有尽有你的高级早餐三明治-餐馆已经成为一种象征和一种好奇心,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吃饭场所。格里芬·汉斯伯里(Griffin Hansbury)说:“我是吃着卷心莴苣长大的,但新一代知道卷心莴苣是所有莴苣的屁股。”他的笔名是耶利米·莫斯(Jeremiah Moss)。《消失的纽约:一个伟大城市如何失去灵魂,记录这些慢慢消失的机构。“对我来说,餐厅是一个非常民主的地方,”他说。但在这个新的、更富有的时代,说每个人都是餐厅评论家是一种时髦的说法,芝麻菜很久以前取代了卷心菜成为首选的绿色蔬菜,这一新的食客阶层喜欢被他委婉地称为“更精心策划的用餐体验”。
“我仍然会去老餐馆怀旧,但我不会太悲伤。著名美食家、纽约市餐饮历史学家亚瑟·施瓦茨(Arthur Schwartz)说。他住在布鲁克林,记录了这些人类学的美食趋势,它们无情地在纽约市的餐饮大草原上移动。和许多研究这一流派的学者一样,施瓦茨对老派咖啡店和“独立的餐厅体验”之间的区别做了细微的(但现在还没有定论)区分。当他长大的时候,那是老市场餐馆在第11大道,林肯隧道入口处——据他所知,市场是曼哈顿最后一家拥有自己停车场的餐厅。这是一家60年代的餐厅,以其未来主义的、斯普特尼克式的设计而闻名。自从2015年该市场关闭,为一座13层的豪华建筑让路后,施瓦茨说他现在可以用两只手数清外部区剩下的老式恐龙汽车餐厅的数量。施瓦茨认为,独立餐厅的热潮可以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当时一位名叫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的先驱开始在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的街头,坐在一辆现代马拉餐车的后面卖餐点。这一行业的鼎盛时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状像火车车厢的闪闪发光的预制结构被运往新的州际高速公路系统的每个角落。但在纽约市,先驱是希腊街头小贩,他们在市中心用手推车卖糖果,然后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进入糖果店,从那里进入了更持久的食客和快餐咖啡店的世界。
一些古老的希腊家庭已经转向了稍微高级一点的餐厅(利瓦诺斯(Livanos)家族在怀特普莱恩斯(White Plains)和市中心的高档餐馆一起经营一家小餐馆Molyvos而且Oceana),还有许多人已经放弃了这项业务。一些食客精明地适应了当地的风土,从而在城市中繁荣起来Veselka在东村,那里以乌克兰汤和饺子而闻名,还有它的餐馆功能24小时停止加油邻里聚会的猎狗,还有Lindenwood餐厅在加勒比风味浓厚的纽约东部,这里供应早餐鸡蛋,里面堆着炸优卡或甜芭蕉,还有一系列加了轩尼诗(Hennessy)的鸡尾酒——而其他一些餐厅适应得不太好,最终消亡了,就像所有餐厅长期以来的情况一样。
施瓦茨说,在他所在的布鲁克林社区里,这种例行的晚餐早餐仍然是一个受欢迎的小众市场,这可能要归功于一种自由流动的方式泽西男孩- 60年代的怀旧,仿制品喜欢艾伦的“星尘”号餐厅在时代广场,游客们一边排队大嚼20美元的芝士汉堡,一边听一波又一波唱歌的女服务员为他们唱小夜曲。尽管有这样的哀叹,施瓦茨指出,很多老机构应该关闭。他还记得最后一次去埃尔格列柯餐厅(El Greco Diner)的情景。这家餐厅以大餐量和水装饰的俗气内饰而闻名,但在经营了40年之后,它在几年前被拆除,为另一个共管公寓开发项目让路。“我们像所有人一样,开车出去表达我们的敬意。坦白说,那是一团糟。沙拉难吃极了。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得到任何食物,最后我们走了出去。”

与此同时,那些从餐馆末日中幸存下来的精明人,尤其是在曼哈顿,一有轻微的麻烦迹象就会退缩,并小心提防。“我们正努力延续这一传统,但它已经所剩无几了,”乔希•科内基(Josh Konecky)说。他是一位和蔼可亲、身材魁梧的绅士,目前正在跑步艾森伯格的三明治店自1929年以来,这家店一直在第五大道下侧22街和23街之间的西北侧兜售各种各样的美食。科内基与这栋楼的两个房东之一,一位上了年纪的食量大的人根据他们的协议,他每次来的时候都要为菜单上的任何一道菜付两美元。但那个房东大约五年前就去世了,而另一个住在康涅狄格州,对鸡蛋三明治没有任何兴趣,一直没有表态。科内基并不打算出售,但他会注意合适的报价。
尼尔咖啡店的老板克里斯托·卡洛迪斯(Cristo Kaloudis)在列克星敦大道(Lexington Avenue)和第70街(70 Street)的街角占据了同一个位置,已经超过70年了。他希望通过把生意交给儿子来避免类似的问题。“时代在变,我是一个守旧的人,”卡洛迪斯说。他在60年代从基奥斯岛来到这座城市,在森林山的厨房里工作,37年前接管了尼尔餐厅。小角落里的l型餐台看起来就像原来的尼尔时代的东西,还有那些渐渐褪色的乙烯基小隔间。大多数早晨,这些隔间里都坐满了从街那头的亨特学院(Hunter College)来的学生、休息的门卫和维修工,以及各种退休外交官和来自白领社区的华尔街有钱人。我父亲把尼尔餐厅视为自己的非官方餐饮俱乐部,称他们为“当地的老贵族”。他经常在周末的早晨带孙子们去体验那种古老的、精心设计的早餐高峰仪式,就像邻居里的其他长者拉着他们的孩子去这座城市的博物馆一样。
今年将满80岁的卡洛迪斯说,他本可以在多年前买下这栋楼(“82年的价格是100万美元。谁有一百万美元?”),几年后租约到期时,要由他受过大学教育的儿子尼克(Nick)重新协商。根据食客的习惯,他多年来不断增加菜单,以适应餐饮时尚的变化(“我们现在有牛油果奶昔,”他耸耸肩说),但他也承认,在这个利润率不断下降的时代,储备这么多菜的食材——无穷无尽的选择是食客用餐的心理享受之一——并不容易。他最畅销的低利润产品是鸡蛋,菜单上有29种制作方法。每天,尼尔餐厅要消耗30磅绞碎的牛肉,其中大部分用来制作22种不同的汉堡搭配,还有肉馅卷和现做的肉酱。
卡洛迪斯说:“除了炸薯条、牛肉陀螺和冰淇淋,这里没有什么是冷冻的。”如果你想了解像他这样的手术的困境(以及天才),看看不起眼的火鸡胸肉就知道了。在尼尔餐厅,他们每天早上烤一块20磅的鸡胸肉,用来做火鸡俱乐部三明治、火鸡汉堡、火鸡牛油果卷(“新添加物”区12.95美元)、火鸡美食(“美食美食”区14.50美元),以及经典的火鸡晚餐(配土豆泥和肉汁16.95美元)。但随着火鸡价格的稳步上涨(从两年前的每磅3.40美元涨到4.25美元),盈利越来越难(“我们这里的价格很低。我从来不养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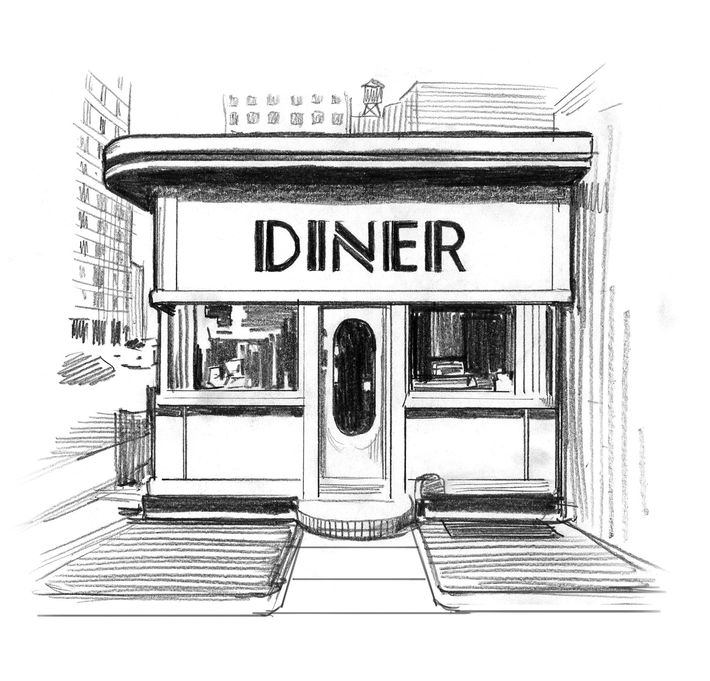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高档餐厅的圈子里,在迎合芝麻菜一代口味的厨师中,用餐者的仪式从未像现在这样受欢迎。“我喜欢这些行话,我喜欢这里的食物,我喜欢当你进门的时候,服务员叫你‘亲爱的’,”威利·迪弗雷纳(Wylie Dufresne)说,他以分子烹饪的先驱而闻名,现在正把这种方法应用到精心味甜甜圈在他最近开张的威廉斯堡咖啡柜台.他认为快餐烹饪和烧烤是美国对国际烹饪经典的最大贡献,他能背诵出那些银色建筑的名字——Haven Brothers和位于普罗维登斯的Ever Ready Diner——这些建筑在他年轻时曾点缀在高速公路上,就像航海爱好者能勾出20世纪初消失的大型远洋轮船的名字一样。
“当我看到这些餐馆关门的时候,我很害怕,因为他们一走,就不会再来了,”最近一个周二的早上,我们坐在格拉梅西公园第三大道的小乔餐厅(Joe Jr. Restaurant)的柜台前等待我们的早餐时,厨师说。这家Joe ' s(据传说,直到70年代中期,这两家Joe ' s的主人是同一个人)近年来因其6美元的芝士汉堡的质量而闻名,但迪弗雷纳从街那头的朋友神学院高中(Friends Seminary High School)的学生起就一直是这里的常客。他每个月至少和家人来这里吃一次饭,他喜欢带外地的超级厨师朋友来,比如诺玛的René Redzepi,品尝他最喜欢的一餐——奶酪煎蛋卷配香肠、土豆饼和鲜榨橙汁——并观看厨师们在煎锅上打散鸡蛋、将蛋壳扔进背后的垃圾桶的永恒芭蕾。
迪弗雷恩最喜欢在工作日的早上去Joe 's,尤其是周二,因为此时的厨房没有因为周末而感到压力或宿醉,但仍有周日繁忙的节奏。当他最喜欢的厨师马科斯(Marcos)准备我们的早餐时,迪弗雷纳小心翼翼地把餐巾放在腿上,就像在Per Se餐厅吃饭一样。桌子上坐满了其他的常客:两个休息时喝咖啡的警察,一个优雅的女人,迪弗雷纳说她多年来一直来这里,享受着她的早餐鸡蛋,把钱包放在桌子上。经理Armando Benafort走过来和主厨握手,他们聊起了街对面的Gramercy Café这家突然临时关闭的老餐馆。(“没人会翻新一家餐厅,”另一位常客告诉我。贝纳福特说,他已经在Joe 's做了24年的柜台工作,和日本那些伟大的寿司学徒一样,烧烤师傅马科斯(Marcos)从1992年就在这里工作了。他告诉我们:“要想在烧烤架上做得好,你就得服刑。”
当我们的早餐端上来时,很容易看出原因。这里的煎蛋卷不是你在一些油腻的勺子里吃到的斑点状、半焦的肉馅煎蛋饼。它是完美的淡黄色,鸡蛋在奶酪周围平滑地旋转,迪弗雷纳指出,当你在平底煎锅上做煎蛋卷时,这是不容易做到的。橙汁有一种生动的,甚至是热带的新鲜,还有一些无籽的果肉在杯底愉快地漂浮着。我们一边享用早餐,迪弗雷纳一边回忆着这些年来他最喜欢的餐点:Veselka的深夜汤,第二大道舞台餐厅(Stage Restaurant)的鸡蛋和香肠。这不仅是对某种食物的怀旧,也是对稍不那么挑剔的纽约市的怀旧,那时曼哈顿还是一个工薪阶层聚居的行政区,而且这个城镇确实是24小时营业的。
在那之后,我又去了最后一家幸存的小乔那里吃了几次早餐。一天早上,高峰过后,马科斯在休息时坐了下来——据我计算,他为大约50人做了完美的早餐,外加一些宿醉后的芝士汉堡——吃了一碗希腊沙拉。他说他来自墨西哥南部的普埃布拉,但他现在是纽约人。我们翻了翻菜单,有24种煎蛋卷、小烤牛肝、肉饼,还有一盘盘18.4美元的比目鱼柳。我问他最喜欢吃什么菜。他耸了耸肩,露出疲倦的微笑,就像那个老餐馆的服务员路易(Louie)过去常常做的那样。“你在这里点什么并不重要,”他说。“一切都好”。
Amelia Schonbek补充报道。道具造型由玛丽霍华德工作室的Dorothee Baussan;食物造型:杰米·基姆;包由Mansur Gavriel。
*本文发表于2017年6月26日的《纽约杂志。

